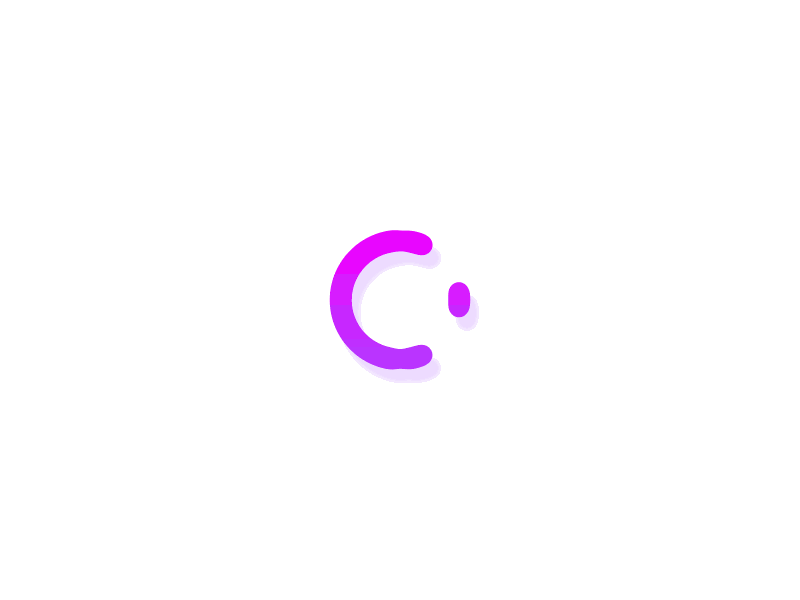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唔,不是。傅城予说,三更半夜不行,得睡觉。 傅城予并没有回答,目光却已然给了她答案。 可是她又确实是在吃着的,每一口都咀嚼得很认真,面容之中又隐隐透出恍惚。 他写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件事,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,可是看到他说自己愚蠢,说自己不堪,看到他把所有的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,她控制不住地又恍惚了起来。 直到栾斌又开口道:傅先生有封信送了过来,我给您放到外面的桌上了。 好一会儿,才听顾倾尔自言自语一般地开口道:我一直想在这墙上画一幅画,可是画什么呢? 她吃得很慢,以至于栾斌估摸着时间两次过来收餐的时候,都看见她还坐在餐桌旁边。 顾倾尔却如同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,没有任何回应之余,一转头就走向了杂物房,紧接着就从里面拿出了卷尺和粉笔,自顾自地就动手测量起尺寸来。 信上的每一个字她都认识,每一句话她都看得飞快,可是看完这封信,却还是用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