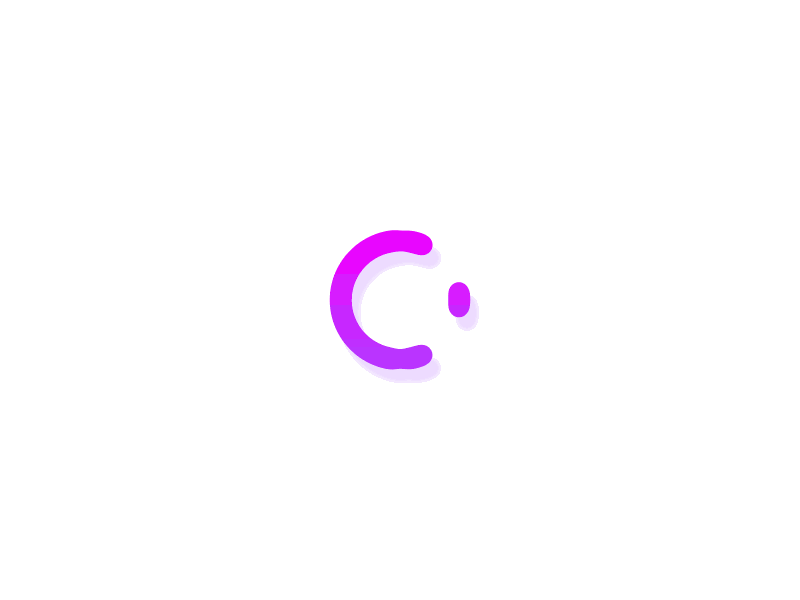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怎么说也是两个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度过的第一个晚上,哪怕容隽还吊着一只手臂,也能整出无数的幺蛾子。 容隽那边很安静,仿佛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。 容隽听了,哼了一声,道:那我就是怨妇,怎么了?你这么无情无义,我还不能怨了是吗? 谁知道才刚走到家门口,乔唯一就已经听到了屋内传来的热闹人声—— 容隽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电话号码从黑名单里释放出来,连忙转头跌跌撞撞地往外追。 那这个手臂怎么治?乔唯一说,要做手术吗?能完全治好吗? 虽然这会儿索吻失败,然而两个小时后,容隽就将乔唯一抵在离家的电梯里,狠狠亲了个够本。 我知道。乔仲兴说,两个人都没盖被子,睡得横七竖八的。 疼。容隽说,只是见到你就没那么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