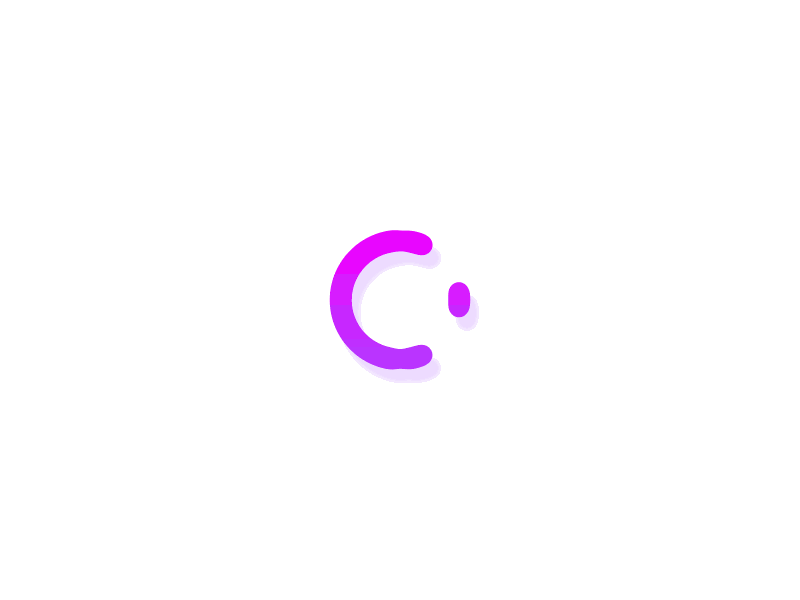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伙伴们,我唯一的要求,就是希望,我们能活到最后。 要不是在比赛禁止说脏话,鸟瞰都怀疑对方早把她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。 苏凉头发有些湿,几滴调皮的水珠顺着天鹅颈一路下滑,滚进被浴巾裹住的身体里,一下子就不见了。 陈稳微微弯腰,摸了摸苏凉的头发,头发还有些湿,他找到吹风机,插好电源,动作轻柔地将人上半身拥入怀里,开着最小档的风,温柔地帮她吹着头发。 苏凉所在的6号小队四人坐在一起, 口述复盘的同时,商量着下一局比赛的打法。 苏凉挑了颗薄荷味的,剥开塑料纸,扔进嘴里,鸟瞰见状,也拿了一颗草莓味的。 开局前,她对着麦克风,只对自己的三位队友,下达了一个这样的命令: 难道医疗兵只能带着药包飞速去救人?狙击手只能躲在暗处架枪偷人头?开车的一定要是指挥?对枪手非要以命换命跟敌人对搏?苏凉摇摇头,我觉得这样太僵化了,一支队伍如果打法固定,战术老套,被反套路的只会是自己。 东西差不多快扫完的时候,她提示陈稳: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东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