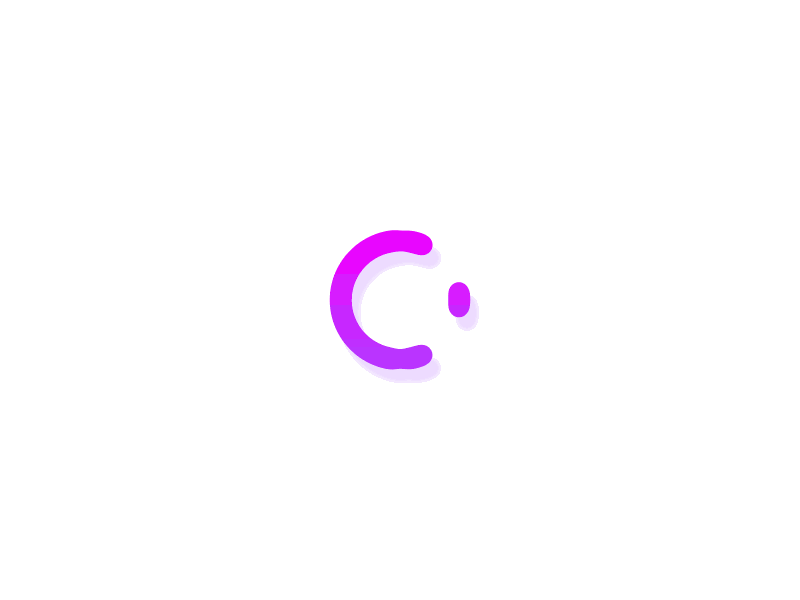
播放列表
正序
内容简介
许久之后,傅城予才缓缓开口道:我也不知道永远有多远,我只知道,有生之年,我一定会尽我所能。 顾倾尔果然便就自己刚才听到的几个问题详细问了问他,而傅城予也耐心细致地将每个问题剖析给她听,哪怕是经济学里最基础的东西,她不知道,他也一一道来,没有丝毫的不耐烦。 她很想否认他的话,她可以张口就否认他的话,可是事已至此,她却做不到。 顾倾尔没有理他,照旧头也不回地干着自己手上的活。 渐渐地,变成是他在指挥顾倾尔,帮着顾倾尔布局整体和细节。 顾倾尔见过傅城予的字,他的字端庄深稳,如其人。 就好像,她真的经历过一场有过郑重许诺、期待过永远、最终却惨淡收场的感情。 可是演讲结束之后,她没有立刻回寝室,而是在礼堂附近徘徊了许久。 现在是凌晨四点,我彻夜不眠,思绪或许混乱,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。 那个时候我有多糊涂呢?我糊涂到以为,这种无力弥补的遗憾和内疚,是因为我心里还有她